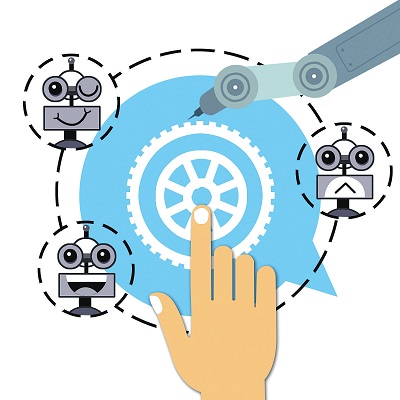在中國古代文化“五行”中,秋屬金,金戈鐵馬。古代征戰用兵,以及民間械斗,多發生在秋季;古代處決死刑犯,也多在“秋后問斬”。周代管理刑法最高的官“司寇”,遂又稱“秋官”。秋季自然界中充滿了冷涼、肅殺之氣,大自然執行草木、莊稼一年一度“死刑”的便是霜凍——樹落葉,草凋零。連人間老弱病人睹物思已,也容易產生憂傷、恐懼的心理,現代抑郁癥也在秋季高發,正所謂“多事之秋”。

其實,白霜對于古代社會危害最大的還是農業上的霜凍災害。霜凍是我國農業“旱、澇、風、凍”四大主要氣象災害之一。歷史上霜凍災害的記載馨竹難書。例如,我國田園詩人代表晉代陶淵明,因為“不為三斗米折腰”,歸隱田園。晚年因失火家境不好,對霜凍災害更有“切膚之痛”。他的《歸田園居二首》中便有“常恐霜霰至,零落如草莽”之句。在舊社會,小農經濟一旦莊稼的收成泡湯,讓他們該如何活?
可是,古人多不知,這種霜凍災害的發生原因卻并非是由水氣凝結成的白色晶體——白霜本身所造成,因而使白霜蒙受了千古奇冤。因為,即使沒有白霜出現,只要氣溫在零攝氏度以下,作物同樣會受到凍害。這種情況,農民形象地稱之為“黑霜”。
原來,造成霜凍災害的罪魁禍首乃是與白霜同時發生的零下低溫,最終使農作物細胞結冰死亡的結果。而且,實際上,當大氣中水氣凝華成霜時,不僅不會吸收熱量降低氣溫,反而因會釋放出大量的凝結潛熱而減緩氣溫下降。1克水汽凝華為霜時放出的凝結潛熱為2794焦耳,實驗數據表明,復霜的葉子其耐一定零下低溫的能力,反而比不戴霜的葉子強些。瞧,貢獻反成罪狀,豈不是“冤上加冤”?
人們一看見白霜,總是與氣溫零下聯系在一起。其實不然,在一些情況下,氣溫即使零下,地面上卻仍然可以無霜。
第一種是干旱地區。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”,根據我的研究,當清晨7時空氣相對濕度低于40%時,即使氣溫零下再多,也不會有白霜出現。1953年4月11-13日,由于北方冬小麥剛剛拔節,恰遇強冷空氣南下,華北大部分地區最低氣溫降到零下1-3℃,出現大范圍嚴重霜凍。在那次嚴重霜凍中,海拔54米的北京最低氣溫0.4℃,地面已經出現白霜,但西側海拔724米的張家口,最低氣溫已低至零下7.4℃,但由于當時相對濕度只有38%,反而沒有出現白霜。
第二種是多大風地區,白霜難結,結了也易蒸發消失。最典型的例子是長白山。山頂天池海拔2670米,山高風大,年平均8級及以上大風日數178.1天,但年平均白霜只有7.9天;而海拔711米的山麓長白,年平均大風日數僅34.8天,而年平均白霜日數則多到174.1天。
第三種是冬季多細雨,而且最低氣溫零下不多的地區。因為有水情況下白霜不易結,結了也易融化掉。例如貴州畢節,年平均白霜日數17.8天,但有雨日子中“零下卻無霜”的日子倒有19.3天之多。
當然,在我國幾千年的歷史中,白霜也不是凈背黑鍋,而是同樣也有因這類張冠李戴而冒受“榮譽”的情況——最典型的是秋天的美景紅葉。
因為,古人們認為秋天的紅葉是由于“霜打”而形成的。例如,明戴縉的“黃蘆千里月,紅葉萬山霜”;清顏光敏的“秋色何時來,萬里霜林丹”;還有“清霜醉楓葉”“西山紅葉好,霜重色愈濃”等,當然其中最著名的可能還要算杜牧的“霜葉紅于二月花”。
實際上,秋末樹葉的變紅也與白霜本身無關,而是低溫使樹木根部吸水能力降低,進入葉子中的水分減少,因而使葉綠素生成少而破壞多,花青素增多樹葉呈現紅色的結果。因為葉子變紅實際上常常在氣溫降到0℃以前就出現了。2015年秋末,海拔489米的延慶最低氣溫尚未低于零度,而海拔僅約百米的香山,2萬株黃櫨40%的葉子早已經紅了。
總之,白霜以作物凍害而蒙受“千古奇冤”,又以紅葉等佳景而坐享“百世流芳”。在氣象學中的其他氣象要素和天氣現象中,大概再沒有象它這樣兼具“功”“過”于一身的戲劇性故事了。(林之光)